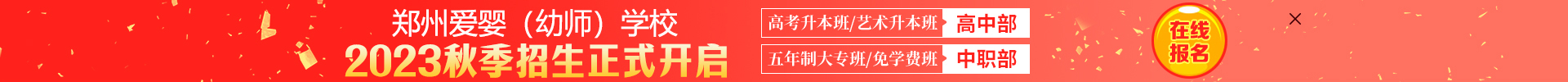 ×
×
發布時間:2022-03-19 信息來源: 瀏覽次數:1910
之所以要談這個話題,是源于當今學前教育的一些現象。
現象一:幼兒雙語熱
課程游戲化項目的推進,首先需要觀念的轉變,要有目標意識,項目的目標不只是環境改造,更核心的是《3—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》的落實和兒童的發展。站在這個高度上,我們才能去檢驗和衡量自己的課程改革是否到位,環境創設是否到位,活動組織是否到位。
現象二:很多幼兒園彰顯著歐美色彩
現在很多幼兒園彰顯著歐美色彩。這些花樣繁多的歐美色彩幼兒園反映了一個問題:我們現在正在自覺成為ABC(American-Born Chinese)。此外,現在的學前教育課程里,海外課程占主流。我在思考這個問題,若干年之后當我女兒有了孩子,孩子若問我:“姥姥,你是研究中國學前教育的,那你研究什么課程呢?”“我研究了一大堆外國名稱。”“那你研究中國嗎?”“寶寶,對不起,沒有。”如果有這一天的話,我會成為歷史的罪人。泱泱大國,難道就沒有一點繼承自己文化的意識嗎?自從我假想這個情境后,我每天都覺得有一種迫切感,有一種時代的使命感在召喚。
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的今天,我們的孩子有多少本土文化認同?幾年前,我去大阪一個幼兒園。當時是三月份,所有的孩子都穿著小短褲,而我穿著厚厚的棉服還在發抖。園長告訴我,這里有個來自中國的小男孩,才來半年,問我要不要跟他說話?我說要啊。這個小男孩過來了,一百個不睬我。園長說他不愿意跟我說普通話,讓我用日語跟他說。隨后,他跟我說話了。那個時候,我的心猛地抽了一下。這個孩子才3歲多就知道在這里說中文沒有自信,很自卑。
另外一件事是此前我在日本一家律師事務所做注冊會計師。有一天我對老板說我接了兩個電話。老板立刻說你怎么可以接電話?我說我為什么不能接電話?他說如果他的客戶知道中國人在這里打工,會全走光的。我當時非常生氣,老板平時以我是東京大學畢業生為傲,但現實卻是如此。這兩件事使我明白如果我們國家沒有足夠強大的話,我們在國際上都會受到被人歧視的待遇。
三年之后,我又經歷了一件痛心的事情。當時,香港教育行政署請我去香港指導一個幼兒園做研究。園里老師告訴我這個孩子就是我們要研究的對象。我進去跟他說:“小朋友,你好。”這個孩子見我說話,第一反應是驚恐地一跳,往后退了幾步。看他這個反應,我跟園長說請孩子媽媽過來。
他媽媽一見面就跟我說廣東話。但我從她的口音判定她不是廣東人。我問她能不能用家鄉話跟我說話。她聽了就流淚了,她說她到香港半年,從來沒有敢在家里跟兒子說過家鄉話。后來,我們見到了孩子奶奶。奶奶是香港人。那就意味著,如果說普通話就比別人低一等。
這個事情在我心里烙下很深的印記。如果在我們的學前教育課程中還一味地以西方為風向標,或許以后這些孩子提起自己中國人的姓都會感到難為情。學術應該有學術的含量,但是更應該有社會責任感。我們要警惕我們自愿成為學前教育的文化殖民。
確立中國文化教育自信迫在眉睫。
我們來看一下時代背景。近來,央視陸續播出了《中國漢字聽寫大會》《中國成語大會》《詩詞大會》《經典詠流傳》《國家寶藏》等節目;暢銷書方面,《顏氏家訓》《曾國藩家訓》《梁啟超家書》一度受到熱捧,這些都是中國文化的結晶。
那么何為文化?何為文化自信?為什么要確立文化自信?如何確立?文化的“文”,甲骨文里是“魚紋”的意思。“化”是滲透。文化是軟實力,是一個民族的名片。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強調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、一個國家以及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,并對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堅定信心。
為什么要確立中國文化教育自信呢?著眼于批判當時的學前教育效法、模仿西洋幼稚教育之流弊。我們可能把別人的自由完全沒有任何約束地模仿過來了。陶行知批評“外國病”“花錢病”“富貴病”等三大弊病,主張創辦“中國的”“省錢的”“平民的”幼兒園。縱觀當今,現在這三種病卻愈演愈烈。一個國家核心的文化是文化軟實力和文化自信。我們每個學前教育工作者都要傳播文化。
文化人類學把文化分成四個層面:第一層衣食住行、第二層風俗、第三層語言、第四層價值判斷。我們基于孩子很小,應該屬于衣食住行層面的假設,做了相關研究。
一是從服裝偏好看幼兒的文化意識。實驗程序是:請幼兒先仔細觀察桌上的8張圖片,并提問:“這里有一些不同地方的小朋友穿的衣服圖片,請告訴我你最喜歡哪張圖片?剩下的這些你最喜歡哪張?
其次,針對幼兒所在幼兒園的老師進行訪談,提問聚焦幼兒園所進行的民族文化類教育的課程設計、家園共育活動開展、家庭教育等。”我們做了哈尼族、蒙古族、侗族、漢族四個民族研究,研究表明喜歡自己民族服飾最高的是蒙古族,占比23.33%,哈尼族的孩子最低,占比7.5%。
第二個研究是從建筑偏好看幼兒的文化意識。實驗程序為:請幼兒先仔細觀察桌上的4張圖片,并提問:“這里有一些不同地方的小朋友住的地方圖片,請告訴我你最喜歡哪張圖片?針對幼兒所在幼兒園的老師進行訪談,提問聚焦幼兒園所進行的民族文化類教育的課程設計、家園共育活動開展、家庭教育等。”
我們選了侗族的鼓樓、哈尼族的蘑菇房、蒙古族的蒙古包和漢族的民居。結果是侗族的孩子喜歡自己民族房子的比較高,哈尼族和漢族的孩子對自己民居的喜歡都比較少。
此后,我們為了了解孩子到底對抽象名詞有沒有概念,讓中班老師拿著蛋糕進教室,問小朋友,你們知道今天是誰的生日嗎?小朋友說不知道。老師說,今天是黨的生日,是中國共產黨的生日。過生日要怎么樣?吃蛋糕。過了十多分鐘,小朋友舉手了,問老師,黨怎么還不來?這聽起來很可笑,但是也反映了學前教育的問題。
我們的學前教育課程里有很多隱喻,但孩子在這個年齡段并不能理解。今天很多中國教育課程來不及思考消化,通常是把人家的課程拿過來變成水生植物,看著好看,卻不能扎根生長。我們真的到了必須嚴格、嚴肅、嚴峻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了。

要做“有根”“有魂”的中國學前教育。
所以,我有一個夢想。我們要做“有根”“有魂”的中國學前教育已時不我待。我們要做陸生植物,而不是水生植物。如何做有根有魂?根在哪里?在今天這個時代,我們要確立中國學前教育自信,絕不是井底之蛙。但同時也不是一切外來的都是好的。所以,一個是我們的傳統文化,一個是要有效地汲取國外文化的精髓。在這個過程當中,我們共同構建文化自尊和自信。
基于本土文化的實踐探索,我在國內幼兒園看到了一些非常好的做法。比如剪紙、青花瓷、將相和、扎染蠟染等,通過傳統文化的浸潤熏陶,逐漸培養孩子的民族文化認同。此外,我們還做了食育研究,即通過食育進行的生命教育。日本在2005年頒布了兒童基本食育法,但是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課程。所以,我們意圖進行食育課程建構,讓幼兒通過食育教育在社會文化生態中得到綻放。
食育課程建構分為認知水平、情感水平和行為水平。認知水平方面,能辨別安全食物、遠離垃圾食品。情感水平方面,能歡然接受營養食品,拒絕不良食品。行為水平方面,能更多親近自然,親手種植制作食物。
陳鶴琴先生說,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活教材。讓孩子走進大自然,實行自然教育,認識到植物的生命力,對生命充滿感恩。
在現今全球多元文化碰撞的背景下,如何培養幼兒具有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感,并在此基礎上以包容開放的心態接納其他民族文化,從而形成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?進一步確立學前教育文化自信的思考包括:空間的思考、時間的思考和路徑的思考。
空間的思考上,基于文化生態學的角度,生于斯,長于斯,我們陸生植物的發散是屬于這塊土地的。縱觀全國的幼兒游戲差不多都分為生活類、服務類、財商類這三類。一碗湯,深圳廣州是餐前喝,上海江浙是邊吃邊喝,黑吉遼則是飯后喝。一碗湯能喝出這么多文化特色,為什么我們的課程、游戲要全國大一統呢?
我們是不是應該在自己的土地上考量課程建構?一方面要從近代教育思想中汲取營養,如陳鶴琴先生的“活”教育思想。另方面要尋源文化傳承,汲取傳統文化中蘊含的精神精髓和價值判斷,讓世界認可蘊含中國文化的學前教育。
同時,我們中國的學前教育要蘊含文化的世界性。我們有責任把0—6歲孩子在我們手中培養成有社會責任感、社會道義的公民。我們吹響了學前教育的集結號,就是基于活教育理論的學前教育課程建構探索。
實施“有根”“有魂”的中國學前教育的最大目的在哪里?這正是陳鶴琴先生所說的培養現代中國人。這里,我征得陳鶴琴先生后人同意,把“人”改成“娃”,倡導培養現代中國娃:要有健全的身心、要有建設和創造的能力、要有合作的態度、要有服務的精神、要有世界的眼光。
文章來源于網絡,如有侵權,請聯系刪除!